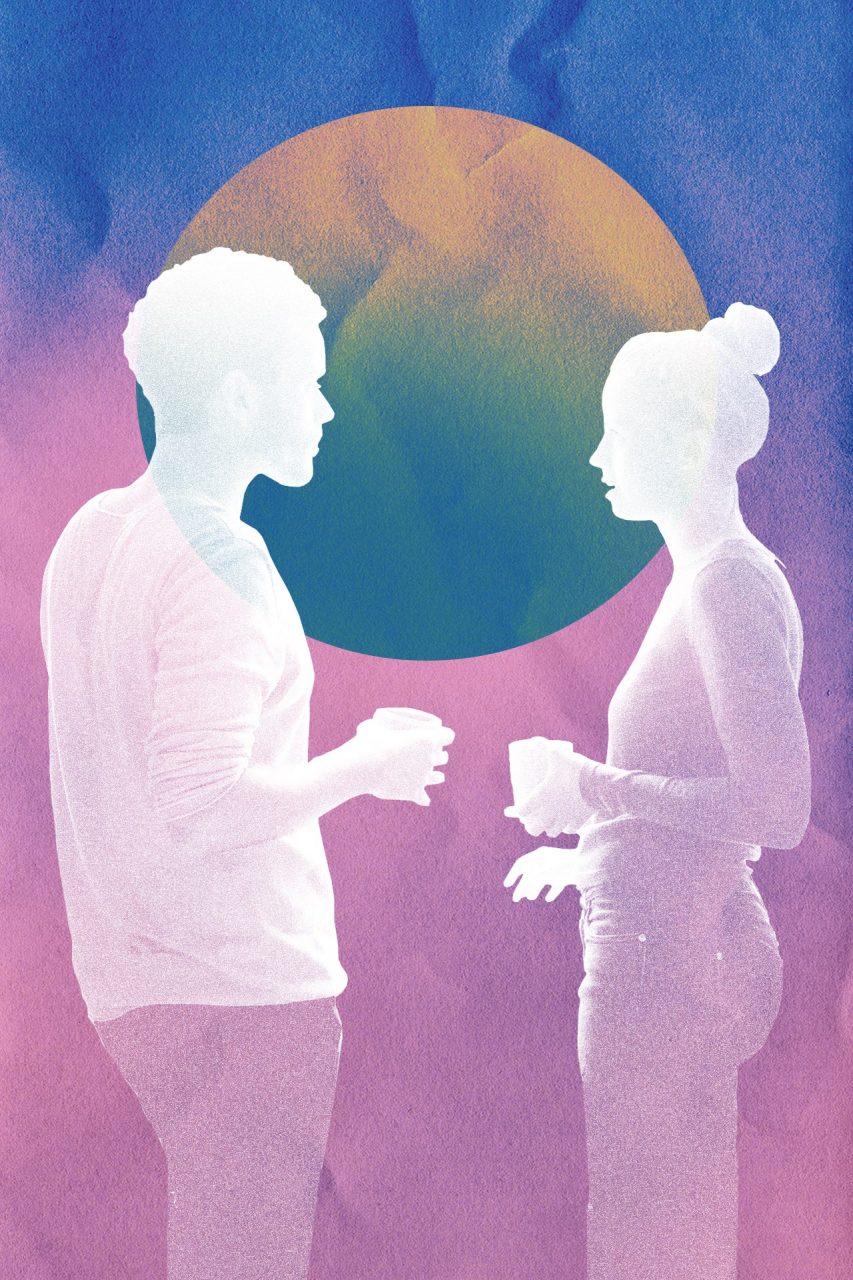
「至少他沒有和一個女孩在一起。」當我打電話告訴媽媽我撞見了去年夏天甩了我的前男友時,媽媽如是回答。
「但我穿的是黑襪子,配的是白色運動鞋。」
「我相信你看起來很可愛。」她試探道。
比我看起來多麼糟糕(沒塗睫毛膏)更糟糕的是,我居然想躲開他,只是因為他大聲地喊著我的名字,我無法裝作沒聽見,所以才從樹籬後面伸了頭了出來。
「你剛才是不是想逃跑?」他問我。
「是啊,我想是的。」
「哦,這麼嚴重,是嗎?」
我最後一次見到Joe是在10個月前。我們本來要去參加一個朋友的聚會,但我們喝醉了,反而發生了關係。早上,我們去吃了個煎餅,我們表現得很造作:所有的愛都是自以為是的,Jennifer Aniston的那種方式。他告訴我,我的臉上有番茄醬。 「哪裡?」我問,他吻了我。 「那裡,」他說。
我讓他吃了我一半的薯餅,因為他忘了下單一個,然後他告訴我。「我覺得我還沒忘了你。」我們本來要回到我的房間看《Succession》,但是… …我們卻做愛了。他走的時候,我看著他的影子從我的門下溜走到外面的世界,我覺得很害怕。主要是因為他說過會給我發短信,我知道他其實不會,但也因為這意味著我不得不面對所有朋友的未接電話以及「你什麼時候到」的短信。
自從Joe用那條從未到達的短信傷害了我之後,我就一直在幻想著再次見到他的完美場景。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是我穿上短裙跟另一個男人約會。在我的幻想中,我會穿著閃閃發光的金色吊帶裙和蛇皮過膝靴。我會和一個他「有點認識」的人一起出現在酒吧——不是「認識」,因為我去那裡做了什麼錯事,而是足以讓人感到刺痛,就像他們在學校裡是同年同學,或者他是朋友的朋友。他的眼睛不知為何比Joe的眼睛更藍,而且他對黑格爾有更多了解,酒吧里的每個人都發現了這一點,因為他巧妙地將理論丟進了談話中,而這種方式——奇蹟般地——不會讓所有聽話的人感到無聊至極。有時他看起來像《Love Island》中的Welsh Connagh 。其他時候是《28 Days Later》阿仙奴的Héctor Bellerín 或 Cillian Murphy 。在幻想中,我表現得非常得體,這意味著不能在Joe的視線中接吻,但也許他會看到我們在房間的另一端分享一個笑話。 「哦,你看,這是一個監獄,」這個新來的傢伙會說,因為我們都知道福柯和他的哲學,肉體的力量無處不在,然後我會狂喜地笑,聽起來好像我真的很高興。
但是在現實,我卻穿著黑色的襪子,白色的運動鞋,還有一件沾滿褐色的T恤。也許是宇宙在懲罰我,希望在一個讓我快樂了這麼久的人身上看到如此嚴峻的東西。
除了我覺得自己多麼不受歡迎之外,見到我的前任最糟糕的部分是談話。一切都很僵硬,一片空白。 「工作怎麼樣?你的新房子怎麼樣?你被隔離在哪裡?」 我對他說話的方式,就像我對不喜歡的家人說話一樣。
他看起來也真他媽的不錯。曬得很黑,以至於他手臂上的毛髮和睫毛尖都漂白了。他穿著我從未見過的衣服。藏青色的背心 一些非常漂亮的羊毛長褲。 「這是給誰穿的?」我想問。但我卻走到下一個轉彎處說:「這是我的。」尷尬地,然後我們擁抱了一下,當我們擁抱的時候,我的下巴撞到了他的肩膀上,因為顯然我們在別人的身體上抱了太多時間後,已經忘記了彼此的尺寸。
「再見。」他說,走了。「或者我想我不會。」
在他轉彎之前,我不能哭。但一旦他走得足夠遠,我就讓眼淚從我身上流出來,就像動脈傷口的血一樣又快又急。我覺得自己對他是那麼的過意不去,但後來我看到了他的臉——一張我在床上橫躺了那麼多天的臉,宿醉、入睡、大笑、爭吵、和好、接吻、用一根手指順著他羅馬鼻的筆直斜度往下摸——我才想起自己是多麼的在乎。
後來,在哥哥那裡,當我喝了一杯酒,吃了一些菜,用麵包把酒給補上的時候,我的感覺有點不一樣。即使順利,那會是好事嗎?如果他看到我穿著那件金色的裙子和靴子和我約會的學校老師在一起,而這個老師恰好是Héctor Bellerín的替身,會發生什麼?短信會變成約會,變成性,變成「我喜歡你」,然後一直到爭吵、問題和消失。碰見前男友的時候,只是有一種傷害的方式,然後確保你以後會傷害的方式。
但是,第二天早上,一條短信。 「我昨晚去了一個聚會,」Joe寫道。 「你家裡的朋友也在那裡。南倫敦開始覺得有點太小了。」
「是啊,我昨天去Haringey就是為了躲避你。」
「我想你可以把這套衣服留到下次我們倆的聚會上穿。」
我一回答就知道什麼又開始了。有些事情是很難逃避的。反正他們會回來找你。
原文源於英國版VOGUE
Editor
Anni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