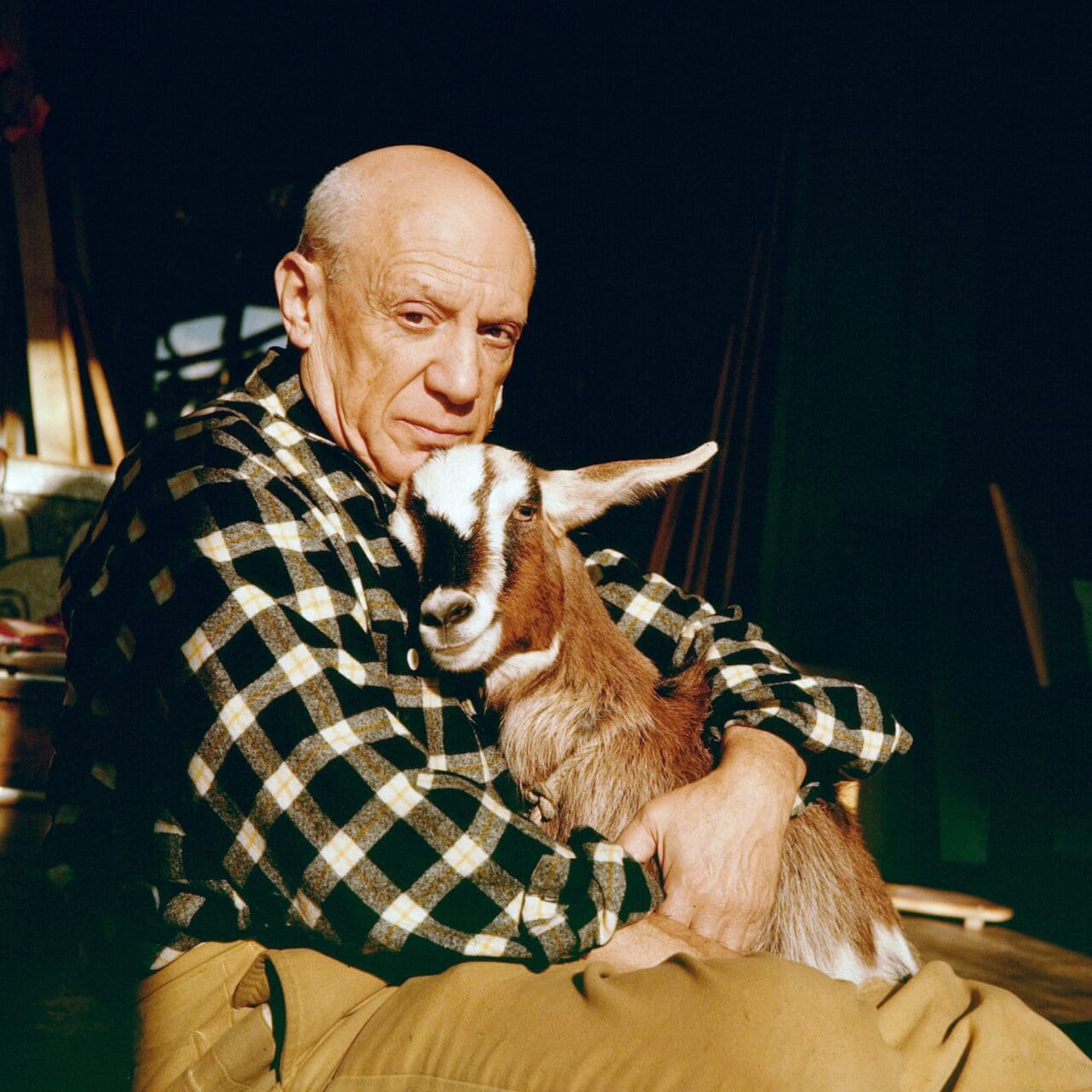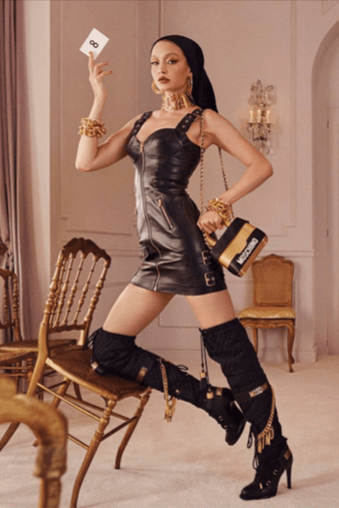早上起床,睡眼惺忪的我瀏覽著Instagram的最新動態。朋友分享女兒生日,浩浩蕩蕩一行十幾人包下郊外的民宿,照片裡是這樣寫的:「這次生日整整慶祝了五天,寶貝們都玩瘋了。」我的單身女性友人則上傳了一張剛做完健身的照片,隱隱約約展露出結實的腹肌,圖片上用跑馬燈的特效寫著:「該為夏天做準備了 #stayfit」。待我無意識地滑完IG,二十分鐘已經過去,嗯,光陰黑洞無誤。
你有社交平台焦慮嗎?在這個世代,大部分的人是有的。根據調查統計,們花在社交平台上的時間越來越多,每天有將近 145 分鐘(也就是將近兩個半小時)的時間我們都在使用社交平台。社交平台讓兩種極端無限延伸,自信高的人,可以膨脹其自我優越,而低自尊的人,會在潛意識與他人比較之下感到更自卑,甚至產生憂鬱或焦慮症狀。
其中又以IG造成的現象最為顯著。IG是社群媒體發展以來,第一個強調圖像和視覺的平台,「文字沒這麼重要,美圖一定要有」的思維,推波助瀾推動了網紅的發展。現在,網紅已經成為人人稱羨的職業選項。在中國有個可愛的用法,叫做「流量小花」,英文則是Influencer,我覺得英文的解釋是相對中性的,強調網紅在某群體中有其影響力。
網紅的力量有多大?
2020年 Netflix 美劇《Emily in Paris》講述一個來自芝加哥、無敵樂觀的女主角到巴黎闖天下的故事。劇情設定從事行銷工作的 Emily Cooper ,時不時與這城市的隨興自拍照,居然讓她在短時間內成為IG網紅。如果說戲劇反映了我們身處的時代,那麼《Emily in Paris》肯定是集大成之影集,因為片中還提及 Emily 因網紅身份,在工作上變得順風順水。
網紅的力量有多大?用Netflix的紀錄片《Fyre: The Greatest Party That Never Happened》來詮釋再恰當也不過。主辦人 Billy McFarland 雄心壯志想在 Palawan 舉辦一場史上最奢華的音樂祭,深諳網路行銷的他,邀請歐美 400 位網紅幫忙宣傳,並找來 10 位超模穿著比基尼拍攝影片,在與世隔絕的小島搭著遊艇在海灘上度假。他們宣傳的標語是:「史上最奢華的音樂祭」。
一張門票就可以過上網紅的生活,這樣的行銷瞬間在IG發酵,48小時內,從一千美金的門票到兩萬美金的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票全數售罄。但因為 Billy McFarland 的好高騖遠,讓這場音樂祭成為了史上最大的笑話,參與的人們從度假變成逃難。比利的員工是這樣說的:「真正的音樂祭,在超模拍完宣傳影片時就已經結束了。」
姑且先不談比利牽涉的行銷詐騙,Fyre音樂祭之所以瞬間受到注目,無疑跟網紅宣傳息息相關。他們將網紅令人嚮往的生活態度放大,這個活動似乎也冥冥之中諷刺了當下社群媒體背後隱含的真實性,到底,讚後的真實是什麼?我們需要如此在意嗎?
真實或虛假
我曾經在出差時遇過一位IG網紅,聊天之後得知其帳號,有著數十萬人追蹤的她從時尚、旅遊到美妝,分享的推文包羅萬象,生活豐富迷人,但我抬起頭來看了她一眼,又回到手機螢幕,心裡納悶,這真的是我對面的那位女性嗎?IG上修圖過頭的照片已經快有詐欺嫌疑了吧。
最近還有一則很有意思的新聞,日本一位中年大叔電單車發燒友,為了讓大家更關注電單車,把他與重機的合影用 Face App 的修容濾鏡,造成網路熱議。不只修圖,還直接改性別,真的很狂。更不用說 TikTok 上的短影片全都配置極為誇張的修圖濾鏡效果,這儼然已成為新世代最迷戀的社群媒體。「自從有了濾鏡之後,我都不需要化妝了。」我認識的一位網紅曾這樣跟我說。

Girls wearing protective face masks due to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are seen taking selfies at the Main Square in Krakow, Poland on April 28, 2020. The rule of covering the nose and mouth in public places with face masks, carves or handkerchiefs came into force from April 16th. The order will not apply to children up to the age of two and people who are unable to cover their mouth or nose due to breathing difficulties. (Photo by Beata Zawrzel/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社交媒體的焦慮和創傷
工作關係時而遇到網紅,外人看來人生勝利組的這群人,不為人知的辛苦和創傷也不少。基本上他們沒有假日,因為要隨時觀測按讚數,也要與粉絲互動。
這個年代,再也沒有像王菲和梁朝偉那樣遙不可及的巨星,要盡可能親和,最好是所有粉絲的網路閨蜜。網紅就算安排私人度假行程也很難悠哉放空,因為不能讓網友忘記你,每每從幾百張圖片裡選出一張最好的,再套個濾鏡和修圖,這樣一做,好幾個小時就過去了。
社交媒體焦慮症有好幾種,一種是上述網紅才有的「困擾」,有越來越多的網紅坦言這份「工作」並不適合自己。澳洲社群名人 Essena O’Neill 便老實說,即便她的一則IG貼文就可進帳港幣一萬多元,但當她發現自己沉迷在虛假的網路世界,靠虛假的完美博取注意力,反而越來越感覺空虛和不快樂。最終,她決定刪除帳號。
另一種通常發生在一般人身上,為了奪取更多注意力,在社群上過度分享自我,並且過度關注他人。這個字也可以跟FOMO(Fear of missing out)一起探討。FOMO中文翻為「錯失恐懼症」,直白點說就是害怕錯過。害怕錯過朋友的聚會、害怕錯過Clubhouse上與名人在同個房間閒聊的可能,害怕錯過朋友發的任何動態……。

COPENHAGEN, DENMARK - AUGUST 10: Mie Juel wearing knitted brown dress, white bag and Marie Hindkær wearing withe and brown checked dress in a Christiania bike outside Ganni during Copenhagen fashion week SS21 on August 10, 2020 in Copenhagen, Denmark. (Photo by Raimonda Kulikauskiene/Getty Images)
該怎麼面對這些焦慮?最關鍵的,就是理解臉友或IG友並不是生命裡最重要的人,如果他們是,那就更無需焦慮,真正的友誼不需要靠社交媒體聯繫,你不會因為少看一條朋友的動態而友誼告急。人生不是很長,還是要浪費在真正值得的人身上。
成為網紅或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當然有很多不言而諭的好處,我也希望自己的IG追蹤人數能以倍數成長。即便如此,我始終覺得社交媒體只是加分題,就算沒加到這個分,你要知道真實生活裡的自己已經足夠高分,就不會再為想成為網紅的焦慮情緒而心亂如麻了。
《台女Tai-Niu:最邊緣的台北女子圖鑑》,大塊出版
原文轉自《VOGUE 》台灣版
>> 立即訂閱電子書及紙本實體書click here
Editor
NICOLE LEE